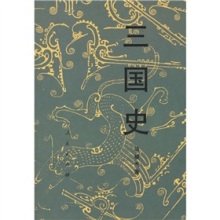武侠.历史-第10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8、牌尾:太平军称战士为牌面,军中老弱幼小为牌尾;
9、圣兵:太平军最小的职务,就是小卒;
10、贞人:太平军称妻为贞人,妾为小贞人。
………【(二)】………
无锡城外,后宅,拂晓。(看小说到顶点。。)
弥漫在河道田野间的硝烟随着晨雾渐渐散开,数不清裹着红巾黄巾,或打着青布包头的尸体,或偃伏、或横陈,或漂浮,横七竖八地,布满了水面、堤头和垅间,有的面目已腐朽,发出阵阵刺鼻的腥臭,有的却还汨汨流淌着鲜血,百丈之间,清人石卡与太平军土垒对望,烟熏火燎、千疮百孔的杂色旗旙,在秋风中扑簌簌地飘扬着。
太平军一侧的土垒后,慕王袍袖被枪弹穿了两三个窟窿,腰带上斜插着短洋炮,手里拎了杆两尺长的胜旗(1),脸色铁青着,不时用旗尖狠戳着土墙;一边的沙包后面,比王舒着条血淋淋的左臂,一面让小把戏包扎,一面龇牙咧嘴地咒骂着:
“X个龟孙,这帮妖崽子,打硬是打不得,就晓得靠洋枪洋炮壮胆,三天三夜了,这个仗打得硬是——哎唷,我X你个小鬼,轻点儿!”
康王恨恨地望着不远处塘河上,几条乌黑的船影:“唉,本来慕王兄、宁王弟已经打开大桥角妖窟(2),要是趁着手顺一口气儿冲过这几个小小村子,现在早就到了东亭,跟忠王、侍王殿下会合了,这该死的妖炮船!航王叔说来也是老码头了,咋这小河沟沟,硬是过不得么!”
慕王摆手道:“须怪不得航王叔,天兵水师那几条七拼八凑的渔舟,如何当得清妖炮船?”
天将汪有为蹲在一边,一直一言不发地听着,此刻却不由叹了口气:“这清妖炮船且当不得,洋鬼子的火轮船……”
“莫再唠叨了!”比王,汪有为的顶头上司,恶狠狠地瞪了部下一眼:“唠叨有个X用,不想死的早,赶紧给老子掏沟儿去!——哎唷,告诉你轻点儿,宰猪么!”
慕王点点头:“比王千岁道的是,我们冲不动,那些妖崽子便要来寻死了……”
话音未落,便听得对面石卡里一声号炮,五色杂旗,青布包头,一簇簇地涌出,开花炮,劈山炮,洋庄(3),也冰雹一般迎面砸过来。
“XX的妖崽子,孩儿们伏低!”比王顾不得伤臂,一面赶忙跳到沙包后,一面指手画脚地大呼着。
“打!打!莫让龟孙们近前!”康王弯着腰,在沙包土墙间蹿高伏低,身手甚是矫健。
“莫乱放!”慕王伸手拔出短洋炮,双目炯炯有神:“红粉圆码不多,土硝又打不远,放清妖近些再打!娃儿们,悠然些,万事自有天父主张天兄担当!”
原本有些紧张忙乱的兵将们一下镇定下来,纷纷散开,伏低,一双双手,却分寸不离枪绳炮闩,长矛短刀。
“放倒,速把旗号放倒!”
随着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花斑几个天将急促地号令,一面面大小黄帜悄无声息地偃倒,土墙沙包之后,刹那间寂静一片。
“长毛贼跑了,冲啊!”
“先登者有重赏!”
清兵们稍一错愕,便轰然蜂拥欢呼,喊杀声更凄厉,脚步也不由地快了起来。
“当当当~~”
清兵阵后,忽地响起一通锣来,正在冲锋的兵勇们也齐刷刷凝住了步伐。
“X的龟孙,屁大点儿胆子。”康王握着刀柄,狠狠啐了一口。
“不好!”慕王神色忽异:“清妖这是要让炮船……”
话音未落,却见清垒上令旗招展,塘河上那几艘黑乎乎、漆着绿眉毛红眼睛的炮船,一齐启碇,恶狠狠地向太平军阵侧飞驰而来,黑洞洞的炮口也一齐指向了土垒沙包。
天国兵将们的脸色都有些变了:这里塘河俱是土堰,野战仓猝,又未筑炮台,岸上炮位,没遮没挡,是当不住这些炮船上的霰弹的。
“呜呜呜~~~”
岔塘深处忽地胜角(4)声不绝,芦苇丛中,桅杆微露,航王的三色大旗高高扬起。
“通~通~”
比王侧耳听着,苦笑着摇了摇头:
“是抬炮,水师这破船,连子母炮也安不得,航王叔老糊涂了么,这样儿家什,硬要抢个头响,不是找……”见周围诸王都狠狠地瞪起了眼珠子,他才硬生生地,咽下了没说完的半句。
仿佛为的应验比王的话一般,清兵炮船旗号一变,转舵向放抬炮的方向杀去,圆弹、霰弹,也雨点般倾泻过去,航王的旗号在桅尖苇丛间晃了晃,不见了。
“通~通~”
抬炮依旧顽强地响着,却渐渐退向苇塘深处。
“杀呀!”
岸上清兵见己方炮船得势,不由地摇旗呐喊起来,炮船炮声不绝,分作两队,在塘河上划出个漂亮的大圆弧,直向航王退去的方向包抄下去。
“轰!轰!”
几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陡地在苇塘中炸起,一片野鸭起处,那几艘炮船,顷刻间俱被烈焰包裹。
“杀呀~~”
十几条蚱蜢划子不知从何处钻出,划上短衣赤足的太平军水手们高举灰瓶火罐,劈头盖脸地砸向那些烈火熊熊,没头苍蝇般乱撞着的炮船。苇丛、塘河,顷刻间被这冲天大火,和火中清卒们绝望的嚎叫声淹没了。
“哒哒哒哒~~~”
马蹄声促,宁王的红旗马队,已烈焰般卷出阵后,直趋清阵侧背。
“冲,天父看顾!”
慕王扬起短洋炮,一跃而起,千百面熏遍硝烟、染满鲜血的黄旗也雨后春笋般一齐竖起,胜角声,喊杀声,狂澜般卷向清阵。
“冲!让龟孙们瞧瞧!”康王讨过宝马,翻身就鞍,呐喊着冲杀下去。
“孩儿们上!”比王捧着受伤的胳膊,咬牙站在沙包顶上:“散开些,莫吃了洋枪洋炮的大亏!”
岸上清兵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太平军一冲之下,登时立脚不住,潮水般溃退下去。
几个戴红蓝顶子的清将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挥舞着腰刀,没头没脑地劈砍着溃卒,总算把阵脚稳住,列队安炮,准备就地阻击。
宁王的马队忽地一卷,斜插清阵后的石卡,守卡清卒猝不及防,一面用鸟枪洋枪胡乱射击,一面忙不迭地转着炮口。
红旗红巾,倏忽间卷到石卡边,马上健儿们纷纷跳踞鞍上,双手先锋包(5),鱼贯掷入卡中。
“轰!轰!”
卡里的火药桶被引燃,石块、木条、旗帜、肢体,被爆炸的气浪不绝抛向天空。
“杀!”
熊熊火光中,宁王九尺九寸长、六十一斤重的春秋刀湛如秋水。
“杀!”
慕王一马当先,已冲到阵前心,劈手一枪,打翻了几个嗷嗷叫着冲上来的亡命之徒,顺手抢了杆矛子,直杀入垓心去了。
“杀呀!”
漫地黄旗,如秋风般卷过,清兵再也立不住阵脚,发声喊,退潮般向东溃去。
“杀呀!”
马兵,步兵,牌面,牌尾,都被这久违的胜仗鼓舞,一路呐喊着追杀下去,塘河上,天国水师那几条大小不一的划子,也顺流直下,船上水手,一面摇旗,一面跺着脚,使劲地助着威。
“前村石垒坚厚,洋枪、洋枪……”
宁王当先陷阵,本已追杀得不见了踪影,此刻却一阵风卷回来,气喘吁吁、没头没脑地喊着。
慕王望着他手里被打穿两个圆孔的春秋刀,胜旗一举:
“穷寇莫追,就地扎住!”
清人的旗帜已远远地只能辨得颜色,村里除了太平军兵将,就只剩了半圈残垒,一片空屋颓垣了。
一些初上阵的圣兵犹在眉飞色舞地回味着刚才的胜仗,老兵们却已裹好伤口,默不作声地掘起了堑壕。
“花斑,这是何村?”
“禀慕王千岁,此地是梅村,东距东亭四九,西北距锡金七九(5)。”
慕王吁了口气:总算与忠王、侍王大队会合在即,忠王亲临,诸路会剿,这一仗,怕是不会再败了罢?
一阵马蹄声碎,宁王领着几个将佐驰到近前,翻身下马:
“王兄,四周都已踏看,斥候哨卡,也都安排下去了。”
慕王微笑着拍了拍宁王肩头:
“好王弟,不愧是斩过勒伯勒东的独眼龙,今日此仗,除了航王叔的尿壶阵,就该是王弟尔的首功了!”
宁王的脸色有些苍白,听得此言,脸上绽出一丝笑容来,右手却不由自主地捂在胸前,捂在那贴肉密藏的小玉佛上。
张大洲顺着塘河匆匆走来:
“禀千岁……”
慕王皱了皱眉:
“不是让尔去请航王叔过村议事,如何一个人转回?”
“禀千岁,航王千岁有谕:‘天朝水师军律,战非全胜,水手不得过船登岸,这水师军律,还是癸好年间,我亲自拉了许将军面禀东王议定的,我若自身带头犯条,如何服得众?’这老爷子,真是油辣子,越老越辣火。”
慕王笑了笑,旋即又不笑了:
“康王、比王二位呢?如何不过馆和傩(6)?”
几位天将面面相觑,似乎想说什么,却终于一个个都只摇了摇头。
“我伲娘哉,炮好歹勿响哉!”
一座拆了半边屋顶的破屋前,蚕花一面喘着,一面抚着怦怦直跳的心口。
她便是这村里的女孩儿,这便是她的家。
早在官兵前队跑到这村里,拉民伕,拆屋子,修石卡炮台的时候,村里的老老少少,就一夜里跑了个干净,都躲进了村外的苇塘桑林,两三年了,官兵跟长毛,又不是第一回在这里打仗,谁不知道厉害呢?再说,这次还有红头发绿眼睛的洋鬼子,和桅杆尖尖会冒烟的洋火轮呢。
本来大兵们没开走,他们是不会冒险回来的,蚕花这样十七、八的大姑娘,就更不敢了。
可不敢又咋的?炮打了三天三夜,大人可以忍,重病的娘亲,三岁的弟弟,如何熬得住呢?
她定了定神,小心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无人后,这才蹑手蹑脚地摸进屋去,在灶眼里摸索着,去寻自己藏在灶灰中的几个红薯。
“阿唷!”
腰眼忽地一紧,已被不知什么人的一只胳膊从后揽住。
“勿要,勿要哉!”
她哭喊着,使劲地挣扎,那只胳膊很有力,怎么也挣不脱。
“莫叫,莫叫么。”
身后,一个中年男子粗重的外乡口音。
蚕花更慌了,死挣不脱,情急生智,低头一口,狠狠咬在胸前那只大手上。
“啊呀!”
那男人吃痛放手,蚕花一挣而脱,疾步向外便逃。
不料那人身形矫健,竟一抢步,挡住了屋门去路。
蚕花差点一头撞在那人怀里,急倒退半步,定睛看时,却见面前男人约有三十八、九的年纪,一头长发,用红绿辫线挽着,穿一身半新不旧,绣了些蟒蛇的黄粗布袍子,戴两臂叮叮当当,或金或银的镯子,右臂抱在胸前,手背上兀自留着渗血的牙印儿,左臂垂着,臂弯上缠满了绷带,正午的阳光透过半边屋顶洒下,照得他那张被硝烟熏花的脸孔阴一块,晴一块的。
蚕花看得害怕,不由放声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