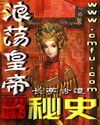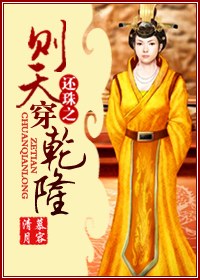乾隆皇帝 - 二月河-第45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两千人的军队无一人骑马,全都是新发的软皮底子快靴,人人衔枚而行,走得无声无息。冷线一样的月亮时而在云中露头,时而又隐进高高的岭背后边。队伍单行行进,足足拉了有五里许长,像一条黑蛇在山谷中蜿蜒游走,依山势时而向北又踅向南,却是毫不犹豫地向西南挺进。福康安自己也是徒步,走在离“蛇头”约半里远近队伍中间。王言保紧随他身边,身上背着福康安用的水、酒,还有一葫芦醋,包里有卷好的葱酱和煎饼、熟牛肉,救急的云南白药、正骨水什么的。他身子不算壮实,已是内衣浑身湿透,咬牙跟着一声不吭。忽然,福康安站住了脚,说道:“水,拿水来。”王吉保站住了身,摸索着晃了晃套着棉套子的水葫芦,失望地说道:“水葫芦口冻结了封口,酒没冻。爷喝一口解解乏儿,成不?”
“酒是洗伤口用的。军令不许饮酒。”福康安的脸映在黯淡的月影里,看不清什么神色,语气干涩单调,略微带点嘶哑,说道:“把醋拿来我喝一口”
这是父亲傅恒的家教,行军一酒二醋三水,醋排在第二。但他不惯这样干口喝醋,一口下去,立时酸得嘴牙咧嘴,却也就满口溢津,不渴了。一手递还葫芦,看着队伍,说道:“前后传话,就地休息半袋烟时辰;不许走动交谈,有屎快拉,有尿快撒——叫前头贺老六带个向导跑步过来!”
长长的队伍挨次停了下来。两个黑影沿着队伍边缘磕磕绊绊到了福康安身边,走在前头是个精干矮个子,操一口四川话,单臂一横,行礼问道:“四爷,您传我?”
“前头又到岔路口了。”福康安看一眼高矗在暗穹里的龟蒙顶,问道:“我们走了多少路?”贺老六道:“回四爷,这几个向导卖力,我们全是抄小道走的,已经走了四十里。离平邑还有三十五里。”福康安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向导:“几时能进城?”
为防误导,他共用了十个向导,队前面六个后边四个,每人分发二十两银子,钱喂足得打呃儿,都是一身邪火铮劲,那向导见问,说道:“回帅爷的话,我们几个都走过,上去右边这道坡就是龟蒙顶的南柏林,下山十里就进平邑,用一个时辰就足够——从这左边向南下去,是祊河上游,一路漫下坡二十里。不过那是夏天走,冬天走河床要跌筋斗儿的——”
“你不要啰嗦,走下坡要多少时辰?”
“回帅爷,要一个半时辰。”
福康安咬着细牙思量了一下,说道:“那就走南柏林。老六,你身子还挺得?”“我川汉一个,身板儿硬,挺得!行军就这‘鬼样子,前头的便宜,就怕后头吃不消!”贺老六道,“依着我说,南柏林虽然近点,还要上这个陡坡。节省些气力,咱们走下头河川,离龟蒙顶也远点,山上不容易听到动静。”说罢望着福康安等令。他是川军绿营里的小棚长,比芝麻还小一点的官,跟傅恒打金川,又打缅甸,军功晋升直到参将。原是他父亲使出来的悍将,傅恒回京前才调任的济南镇守使。福康安到济南时,因贺老六和国泰案子沾包,已经撤差,在家待勘。听说这件事,福康安特地点名“贺老六跟我”,这就带出来了。有这两层夤缘渊源,指挥起来自是加倍得心应手。当下听了贺老六建议,福康安又仔细查看了山势道路,“嗯”了一声说道:“你的建议有理。山上逆贼在南柏林里只要设一小队巡哨的,我军行动就亮出来了。林子里有鸟兽,惊动得又飞又叫,也容易让人起疑。老六,下山你带五十个人急走,进城打前站,先占城北玉皇庙,把驻扎安排下来。我们的人迸城不走南门,要立刻放出便衣哨去——总之一个‘密’字,越密越好!”
“扎!标下明白——天明一切停当!”
“就这样,下令行伍动身!”福康安站起身,又对王吉保道:“你留在这里收容,跟队后走,有伤号跟不上队,天明一律换便衣进城!”说罢随队向南折,隐在夜色之中。
福康安一下山就知道贺老六的建议对头。这里虽然没有路,但一条祊河都冻实了,沿山弯弯曲曲成了冰道,不但平坦,星月余光映着也分外爽亮,比之石磕树绊昏天黑地爬陡坡上山不知好了多少去。福康安听着兵士们嚓嚓走在冰上,不时传来“扑通”的跌倒声。传令:“四人一排牵着手走,后边的跟上来”这样一来,不但队伍缩短了一多半,摔跤的也少得多了。那些军士前半夜都是钻着头拼命爬山,此刻走这道一路漫下坡,真如走在泰山“快活三”道上似的,兵器扛在肩上,挽手走得威势。一个时辰出头一点,两千人已经聚在平邑城北的玉皇庙里。顷刻之间,偌大的玉皇庙前后大院、前后大殿、廊间树下,黑乎乎都站的兵,不时传来营棚长官低声整顿队伍、安排就地休息待命的喝令声。
“老六,干得好!”福康安站在玉皇殿前歇山檐下,望着黑沉沉的庙宇说道。幽暗的老柏树影翳遮得他像个朦胧的幽灵,声音显得分外清晰:“这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吉保,你到庙外,冲平邑城打四枪!”王吉保答应一声,黑地里就跑了出去。贺老六问道:“咱们一路小心,怎么到地方了反而放枪?再说怎么不打三枪两枪,不明不白的打四枪?”福康安道:“‘四’这个数不好琢磨,就要它个不明不白。这是兵荒马乱时分,我们再做的小心,也难免惊动人,放几枪没了动静,反而可以鱼目混珠。”他暗地里孩子气地龇牙儿无声一笑,问道:“庙里有多少道士?”
“六个。”贺老六道:“全都押在神库①里,他们还以为山上土匪下来了呢!”
①神库:庙宇内存放破败损毁了的神像器物的库房。
“等天亮我见他们。从现在起封庙,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士兵没有我的军令擅自出庙的格杀勿论!”
“是!要有香客上庙进香的怎么办?”
福康安拧着眉头想了片刻,说道:“零星香客进庙就扣起来,打完仗再放人。”伸出二指举起手道:“鸡叫天明,不等太阳出来,在庙里再响两枪,火药放足些——外头人听这边响枪,谁还敢来上香?”
说话间便听庙门外“嗵”地一声火枪爆响,是王吉保在外头开了枪。大约要装填火药,少时又听一声,共是四声火枪响震,惊得庙外树林里鸦鸣雀飞,乱了一阵又岑寂下来。此时曦光薄曙微映,只见王吉保腰下佩刀、肩上斜挂火铳,一脸得意进来,禀道:“四爷,我打完了!”福康安看看天色,问道:“有闲人瞧见你没有?”王吉保道:“有个捡粪老头子起得早,在官道上听见枪响,扔下粪叉、粪箕就跑没影了。”
福康安一声不吭便进了玉皇正殿。吉保跟进来,见他双手据案,面对面似乎在审量玉皇大帝的神龛,以为他要烧香祈祷,忙打火点燃了台烛,取香要烧时,福康安摆手制止了他,转过脸说道:“我不信神鬼,信天命。”他吁了一口气,又道:“看来我还不成,走这么点子路就觉得腿疼。我比不上老公爷!”
“爷说哪里话呢!”映着灯光,王吉保觑着福康安脸色,果是稍微有点苍白。他手脚不停,把供神卷案拖到一边,从自己背包里取出一张鹿皮褥子铺上了,忙活着说道:“奴才带这个,爷还要叫我轻装扔了,这会子用上了不是?——奴才爹说过,老公爷面情上头对爷们严厉,见了爷们,一副钟馗相,心里着实看重您呢!那年在枣庄打一仗,老公爷背地怎么说?”他学着傅恒拈须微笑模样,“‘嗯一一孺子可教!’他老人家还说:‘似乎强过赵奢之子了!’——我不明白这意思,有一回纪中堂来府,我问过他的书僮小马子,小马子说:‘你不读书,连赵奢都不晓得?赵奢就是廉颇——《将相和》戏里那位大将军,甘四史里头的有名上将!’您将来呀,准又是我们大清的廉颇外加蔺相如!我们四爷那还了得!”
福康安起初还肃然敬聆父亲的话,听到后来,王吉保连史带戏、连人带事都搅了一锅糊涂汤,比了廉颇又加蔺相如,都一古脑揉进来浑奉承,不禁笑得浑身直抖,道:“想必你一定以为赵奢的儿子比他老子强了……你这浑虫!比你老子加倍的浑……”笑了一气,觉得身上松乏了许多,看看庙殿里无可坐处,只好欠身上神案,以手支颐歪着,看着灰蒙蒙的殿顶出神。
这是他第四次带兵作战了,枣庄一战生擒蔡七,安立一战歼灭王伦,宁夏一战踹了马定钧造反回众老营,歼敌三千献俘七百,乾隆朝野已隐隐有名将之称。就他自己心中划算,比着父亲还差着老大一截子。毫无疑义,老公爷在诸子之中是最赏识他的,一条是文有过目不忘之才干,武有出奇制胜之勇略;一条是扎了根儿的傲睥万物,超拔不群,因此“牢记赵括、马谡”这六个字几乎成了见面必谈的家训。因此,尽管见了人仍旧一副目无下尘的样子,心思却真的是越来越细密小心了。打枣庄是突然遭遇,临机处置;打王伦、马定钧都是大兵合围,他率先锋突袭成功。但这次龟蒙顶之战与前不同,官军占天时,王炎、龚瞎子占的是地利,四周是山,寨中有匪,一个失措,整个鲁南就会糜烂了局面。双方都是有备而为,他喜欢用炮,但大炮根本就拉不到平邑来。四面围困,算了算至少要用七万兵力才能困死龟蒙顶,不但调度艰难,且是守不住密,一旦反众提前突围,上孟良崮与土匪汇合,下海逃跑,那就一切全完。
……他抚着发烫的脑门子再三检视自己的计划,十门红衣大炮调到龟蒙顶北麓,正面猛轰王炎的北寨门,三千军士由界碑镇鼓噪攻击,王炎决计不敢东进,向西一出山就会溃散,唯一的逃路就是从平邑向圣水峪,再入微山湖,与官军周旋。他急急带兵强行军潜入平邑,也就因为平邑那一千多官军根本不是反众对手。现在已经来了,他心里反而有些忐忑不安,北麓是刘墉坐镇,若是王炎集全寨之力从那里突围,这书生挡得住挡不住?葛孝化这个老滑头守右界碑,这边是指望不上他策应了,反众溃散,他肯不肯带兵拦击?……兵将不熟悉啊……”福康安已想得双眸炯炯,“这是野战,临时拉来营兵凑合,能不叫人悬心?……打完这一仗,一定要请旨去练兵,还是自己带出的兵得心应手……”他劳顿了一夜的人,思量着事情,身上暖洋洋的,朦胧着似乎打了一声鼾,头从时间滑落下来,“砰”地碰在卷案木框上,一个警觉跳起身来。他搓脸顿足活泛着身子,见王吉保端一盆热水进来,说道:“大事没办,几乎就睡着了!这盆水好!”说着便忙洗搓,揩了脸又用青盐擦牙,便觉精神健旺,吩咐道:“你出去传令,道士们的锅用来烧水,让兵士就着吃干粮,吃完饭睡觉!叫贺老六来一下!”
“是!”
王吉保跑去了。一时便见贺老六大踏步进来,当胸一拱道:“四爷,您传我?”福康安看看卷案角上摆着的印信关防、笔墨纸砚,问道:“这个县外头何家岭绿营管带你认识?”
“回四爷,他只是个千总,见过面,标下叫不出他名字。”贺老六道,“去年夏天省城会操,校场上演队,我带的队列最齐整,国泰叫我示范,晚上宴席上又表彰我,把总以上的军官都在场,他应该认识我贺老六。”说着,他骄傲地仰了仰脖子。
福康安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傅恒老爷子在成都阅兵,贺老六大雪天赤膊带兵操演,在傅恒跟前证明“川兵不是孬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