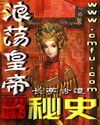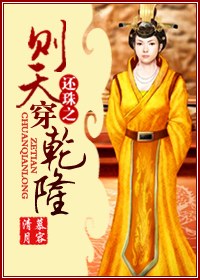乾隆皇帝 - 二月河-第2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很直挺,看样子也在紧张思索。许久,轻咳一声说道:“臣请旨再去一趟江南,亲自彻查兆惠军饷这一案,还有‘一枝花’易瑛,在浙西浙北大湖一带传布邪教,这个祸根不除,皇上南巡安全容易出漏子。刘墉到底年轻不更事,臣放心不下他办差!”
“有子如刘墉,你延清还不知足?”乾隆笑着说了一句,随即敛去笑容,叹道:“尤明堂几次上折子谏阻朕南巡。一是说万乘之君不宜轻动;二是国事繁冗,政务丛杂之时,不宜冶游;三是怕花钱,迎驾送往扰民扰官。他说话梗直不隐,朕从来不罪他,因为他的心地忠正。但两江之地是国家财赋根本之地。一条扬子江,一条运河,还有黄淮堤防,朕身为天下之主,焉能不加关心?就是江南的人文胜景,也应该看看……”
说到这里,他打了个顿儿,江南“人文”其实是指那里汉人聚集,又曾是前明故都,文士墨客荟萃之地,民间草莱之中怀念汉家冠裳制度的为数不少。南巡,可以收揽民心,化解当初清军入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冤情。圣祖六次南巡,三谒明孝陵,接见胜国遗老,其实说穿了就是“羁縻”二字。但眼前五个臣子有三个都是汉人,这一层不能捅破。因此,乾隆略带诡谲地一笑,又道:“扰民扰官的事已屡有旨意,断然不会有的。察勘民情疾苦,顺带观赏江南鱼米水乡风调,朕看也到不了‘荒淫游冶’那个地步儿。刘统勋既然要先下江南为朕清理驻跸关防,也好。你也可在南京休养几个月。查案的事还着刘墉多操办些,你坐纛儿指点指点也就是了。”说罢便起身。
几个臣子也忙起身施礼辞驾。乾隆陡地想到他们一退出去,立即就要封刀去杀讷亲,心里不知怎的猛然一疼。脸上似悲似喜站在座前,怔着没动,也没言语。傅恒小心翼翼问道:“主子还有旨意么?”
“朕是想起一件事。”乾隆暗舒了一口气。已是回过神来,勉强笑道:“江南罢黜那么多官员,该着哪些人去补缺。上次已有旨叫你们军机处议一议,你们是什么章程?”
傅恒原料他反悔讷亲的案子,听是这事,忙笑回道:“军机处没有会议。奴才和阿桂、纪昀三人商计了一下。内务府现在有一百多笔帖式候补待选。这都是些穷京官,在这里苦熬,不如放到江南外任上,内务府的钱粮月例也稍宽裕一点,这件事还没透出风去,请旨之后才能办理。”乾隆冷冷一笑,说道:“太监们早就把风透出去了!如今撞木钟都撞到老佛爷那里去了——早点定下来,只怕那干子急着补缺的笔帖式们还少些混帐钻刺走门路的。你们瞧着,朕还要处置几个有头脸的太监——这上头绝不手软!”因见刘统勋张口欲言,又道:“你好像还有事要奏?”
“臣以为这样不妥。”刘统勋浓眉紧蹙,沉吟着说道:“江南的缺都是州县官缺,是治百姓的,应该让当过百姓的官去补缺;那都是许多人红着眼去争的肥缺,又去一批不懂政务一心捞钱的笔帖式,等于是撵走一群饱狼,又来一群饿虎——”他没有说完,乾隆己是笑了,说道:“你们议的那个不成。刘统勋这才是老成谋国,股肱之臣忠良之心,不愧真宰相啊!傅恒不要脸红,朕没说你们有私意,只是虑事要从根子上虑起,公务忙了,容易就事论事。”傅恒忙道:“这是主子原宥,细思私意也是有的。笔帖式们职在禁苑朝夕见面,他们在宗室皇亲问走动得勤,官虽小,都是手面通天的人物儿,暗自也有怕开罪他们的心。”
乾隆徐步下了御座,却不就离开。在几个大臣的目光注视下,轻缓地橐橐踱步。他的目光变得有些阴郁,望着长廊里映进来的日光,点头叹道:“是啊!这里讲究的就是心……能到这里作事的哪个不是百伶百俐?讷亲素日小心谨密,而方寸一坏,天夺其魄,虽欲幸免而不能!”他目光倏地一亮,又黯淡下来,沉默了一会子挪步便走,边走边说道:“讷亲的事不要等后命了。他写两封血书想见朕,告诉他,见面时彼此更伤心,伤心也不能废国法,见面何益?就这样办……”说着,已是去远了。
乾隆离开流台,过了板桥看表,已过了申正时牌。王八耻随他身后,见抬舆的太监们都垂手站在凉亭子外头候命,抢前一步道:“呆着做什么?主子要到澹宁居给老佛爷请安!”乾隆面无表情,摆手道:“朕累了,随意走几步过去,你们把乘舆抬过那边等着就是了。”
“主子,您瞧这天儿,要下雨了呢!”王八耻陪笑说道,“再说,老佛爷娘娘那边的秦媚媚过来两回了,问主子甚时下来。去迟了,怕老佛爷惦记着。今儿必定有军国大事,主于议了这长时辰的政——也忒劳乏的了。”乾隆说道:“就因为坐得劳乏才想走动走动——议政长短,议的什么政,不是你问的事。仔细着了,告诉下头,这边园子大,要比紫禁城管得更严。朕杀太监可从来没有心软过!”他透了一口气,拔脚便走,却不沿来路,只拣着林间小径向澹宁居方向穿行。王八耻他们不敢随行,又不敢远离,只遥遥跟在后边,绰着乾隆树丛花掩中的影子,时停时走,时快时慢。
天果真是阴了,西边还隐隐传来隆隆的雷声,只是满园的老树薛萝浓荫蔽天,看不见天上的云是怎样的情形儿。乾隆满腹心事,一件一件地想时,却又都不足挂怀,理不出到底为了什么心情如此沉重。思量着逶迤而行,只见林子愈来愈暗,不知名的小鸟在枝桠中扑翅飞着啾啾而鸣,草间小虫也在此呼彼应,浓绿得油黑的树叶丛草掩得卵石小径成了一条细线,越发显得幽暗阴沉。走着,道旁一块卧虎石映入乾隆视线,他触电了似的身上一颤,立即明白了,自己下意识里还在想着讷亲。
这块卧虎石不大,只有一人多高,色彩黑黄相间,天然的四腿屈卧,有头有尾,耳目宛然,据说是壅山山神,康熙初年圣祖出获西苑,它不合自动出来护驾,被圣祖误为猛兽射了一箭,就地化作石虎。后左腿上一块小石疤就是当年留下的箭伤。乾隆小时候常来这里爬上爬下地玩,就在这里海子边的丛石中和讷亲捉迷藏,逮蝈蝈儿,有时还踩着讷亲肩头骑上虎背左右顾盼,讷亲和老总管太监张万强一边一个,扎煞着双臂怕他有个闪失,讷亲那张紧蜜眉头,又惶急又担心的脸,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此刻,讷亲囚在丰台,盼着想见自己一面,忧急如同焦焚,自己却送了一把刀过去!乾隆想到这里,心像从很高处跌落下来,一直往下沉,沉……他的脸色也苍白起来。
正没做奈何处,乾隆忽然听见石后有个女子声气,暗着嗓子极压抑地嘤嘤啜泣,这啜泣给这黯黑的林子里平添了几分凄迷和阴森。他放慢了脚步,手攀藤萝绕过卧虎石头,从虎项下向西看时,却是睐娘偎坐在一株老乌柏树下,背对着石虎,用手帕子握嘴掩面在吞声儿哭。乾隆怔了一下,似乎想蹑脚儿过去吓她一跳,又止了步,轻咳一声道:“睐妮子,受了谁的委屈了?一个人躲在这林子里哭?”
“是万岁爷!”睐娘吓得浑身一哆嗦,转脸见是乾隆,就势儿翻身便叩头,呐呐说道:“没,没人……给奴婢委屈……是奴婢自己想不开……”
“你还敢哄朕?”乾隆一笑,虚恫吓道,“朕都知道了!”
睐娘惊得脸色惨白,用惶恐闪烁的目光凝瞩着乾隆,半晌说不出话来。乾隆原本不在意的,此时倒真的上了心,认真问道:“出了什么事?你说的不对。皇后已经说过,要给你开脸,进‘答应’位,有什么‘想不开’的?”睐娘泪眼模糊低垂了头,说道:“老佛爷方才传了我去……”
“老佛爷?!传你?”
“老佛爷问我,在魏清泰府里,几岁进去的,几岁出来的。”睐娘拭泪道,“奴婢起初也不上心,就如实回了。后来老佛爷又问,听说魏清泰有个外孙,叫黎登科,是几岁上头死的?得的什么病死的?还叫我说实语、不说实话就打我辛者库去。还说……先头有个叫锦霞的,私自勾搭皇上……说我不同锦霞,跟皇上没有伦常辈分的分说,只要说实话,一定不打不撵……主子啊!黎登科是跟他表姐巧姑娘相好儿,夏天吃冰湃李子得了夹色伤寒死的。死时才十四岁,死时候还叫巧姐的名儿——这魏府没人不知道的,我那时才九岁,任事不懂的洗菜丫头,这事跟我什么相干?……主子,主子……你是知道的……我给你的是干净身子……”她说着,已是泪如泉涌,只浑身抽搐着缩在树下,瑟瑟抖动。
暗幽的林于似乎片刻之间亮了一下,接着便是“轰隆”一声雷响。刷刷的雨声急骤如奔马呼啸渐渐近来,密不分个地打得树叶一片声响。只是因大树枝叶稠密,难得有雨滴零星滴下来。王八耻等人闻得雷雨声早已赶过来,见乾隆置若罔闻,忙又远远退了回去。
乾隆的脸色比周围的景色还要阴沉。牙齿紧紧咬着,腮间肌健都微微凸起。他为一国至尊,先是与信阳府的王汀芷有情,汀芷嫁人在京尚偶有来往,她丈夫却无端被人远调了两广,还有嫣红和英英,与汀芷一样于自己有救命之恩,也在园子里防贼似的幽居数年,如今又比出一个锦霞,不知是谁又要害面前这个睐娘了!政务丛杂国事繁冗间,有几个红颜知己聊慰寂寞,怎么处处都有人作梗挡横儿?怨皇后?皇后床上情事有限,从不兜搭霸揽,一心要作史上名贤皇后;怨太后?他不敢这样想,太后管自己的闲事从来循着礼法,又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再没有半点外意的……思量着,乾隆说道:“睐娘不要哭,你干净,朕知道。朕亲自给你作主,看是谁敢伤你!”说着,提高了嗓子喊道:“王耻过来!”
“奴才在!”王八耻听得叫自己,三蹿两蹦飞奔过来,打千儿道:“万岁爷有什么旨意,奴才即刻承办。”
“你给朕查一查,是谁在老佛爷跟前嚼睐娘的舌头,回头奏朕!”
“扎!”
“传旨内务府,哦不,传皇后懿旨,睐娘着进仪嫔,隔过‘答应’这一层,赐名号——嗯,就叫魏佳氏——她是汉军旗,抬入满洲正黄旗!”
“啊——扎!请旨,魏佳氏抬旗,魏清泰家抬不抬旗?”
乾隆略一思索,说道:“一起抬旗吧——他们跟着沾点光,也许少些是非。”说罢又吩咐,“送睐娘到娘娘宫里,把朕的旨意说了。”睐娘发着怔,未及谢恩,乾隆向她一点头,已踅身去了。
出了林子,乾隆才知道雨已经下大了,站在一株老柏树下,由着大监们给他披上油衣,换了鹿皮油靴,在苍苍茫茫的雨幕中淌着潦水缓缓直趋澹宁居。在丹墀上脱衣换靴时,殿中太监早已一拥而上,说着“老佛爷请主子里头更衣,外头风大气凉,防着着凉了!”乾隆摇头不语,到底穿换停当,才跨步进殿。
这里自康熙晚年倦政,一直都是皇帝夏日议政见人的处在,里边的陈设布局仍旧是昔时格调。乾隆一进来,所有的太监宫女轻呼一声“万岁”便都跪了下去。
“都起来吧。”乾隆无所谓地一摆手,吩咐一句:“太后在这下榻,这个须弥座摆在正殿不合适,叫人把它移出去。”说着便进东暖阁,见那拉氏和钮祜禄氏都侍奉在太后榻下,也是刚刚起身,正在蹲福儿。因见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贵妇人也在旁边,炕桌上还零零散散堆着纸牌,料是她们斗纸牌正在玩儿,乾隆也不理会,只向太后打个千儿行礼,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