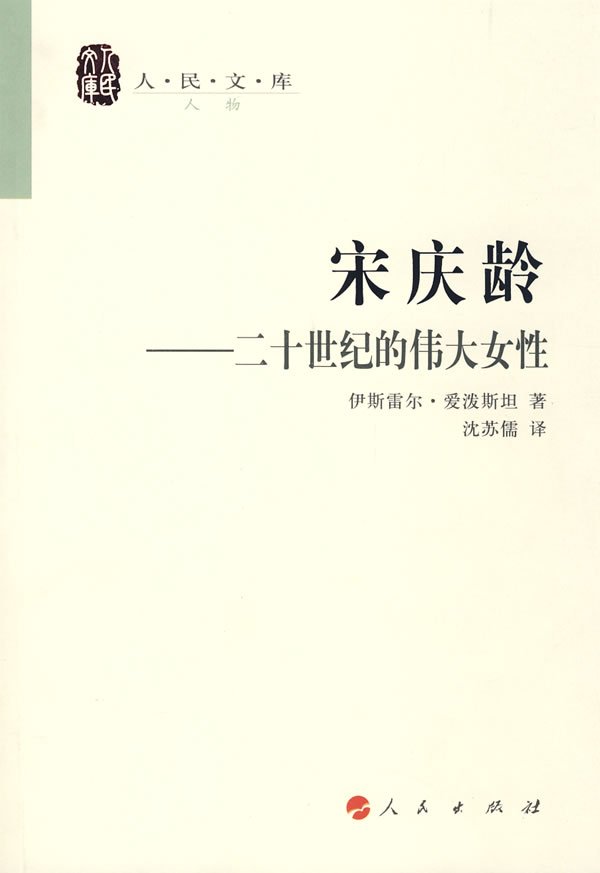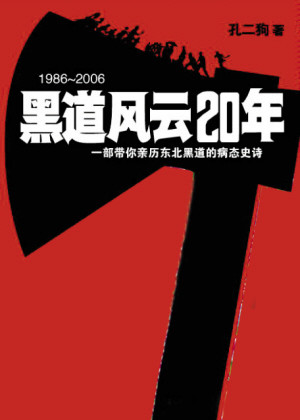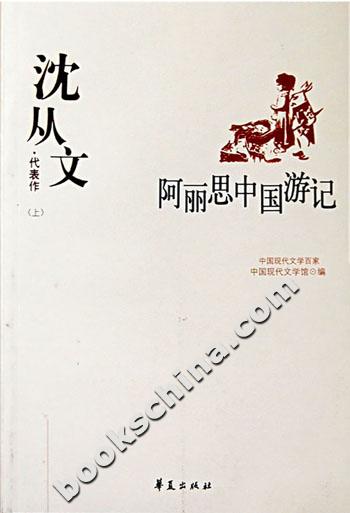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第15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骗子。说把你判无期徒刑、判枪毙、千刀万剐了你,也解下了我们对你的仇恨。……在邯郸我的住处外街道上、理发店拒绝为我剪头发;走在大街小胡同,常有砖头瓦片向我头上飞来……”那时,一个生龙活虎的刘真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办了离休手续,决定远飞他乡。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悲哀。
从1990年赴澳大利亚一晃五年,刘真仍在写作,其中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发表在深圳的《黄河春秋》杂志上。在她已写就的作品中,有小说、纪实小说,还有回忆录。她说,今后只要活一天就写一天。1994年岁末,笔者又接到刘真寄自悉尼的信,她说:“出来的日子越久,越是想念祖国、故乡和乡亲们,我所熟悉的每一棵树、每一条大路小路,和每一道墙壁的砖缝都在想,都思念……”
写到这里,使我想起刘真在《童年纪事》“开场白”里的一段话:“作家的劳动,尤其是像我这种没有多少文化水儿的人的创作劳动,总像纤夫拉着沉重的货船在逆水而上。每写一篇,都像走着一条新航道,脚下道路的崎岖,江河的深浅,每走一步都要重新探索。不管难易,能迈步行走就算是幸运,最怕是船儿的搁浅,怎么也推不动,拉不起了。这样,一时间,作家的艺术生命就像是完结了,终止了。”
路,不管如何坎坷、崎岖,刘真走了过来,并向明天走去。她不停地开拓新生活,不停地去创作。她就像一位不畏艰险的纤夫,拉着长长的流水,流向花的原野,流向金色的季节……
1980年春初稿
1995年1月10日修改
葛翠琳
阎纯德
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这块沃土上,葛翠琳已经辛勤耕耘了40多年。她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一位成绩卓著者。她的创作历程,同中国那些为好几代中国少年儿童所热爱的作家们一样,用爱的乳汁哺育了小读者对真善美的热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建造起人类亲情、民族情、爱国情的圣殿。
葛翠琳是一位换而不舍的追求者,为了给孩子们营造了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她的成就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学创作,一是文学活动,二者组成葛翠琳完美的功德形象。
一
葛翠琳于1930年2月25日(阴历正月二十七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偏僻的小村葛庄。曾用名葛翠林、葛琳、婴林,她用本名和葛翠林、葛林三者作为笔名发表和出版作品。
葛翠琳在《星光闪烁》里说:“我的童年是贫困的,没有穿过一件合身的衣裳,没有见过一种从商店里买的玩具;我的童年是寂寞的,大人为了让孩子吃饱,日夜操劳东奔西走,没有精力顾及孩子;我的童年又是幸运的,一位爱好文学的老师,给我们读许多作家的文章,把我们幼小的心灵带进一个美好的境地,使我们了解了广阔的世界,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物。”这回忆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种印记,它可以使人百折不挠地奋进,敢于面对一切坎坷与不幸。
葛翠琳就降生在中国农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贫穷之家,这个家在物质上没有给她什么幸福,但她爱这个给她许多美好的记忆的家。那个偏僻的小村虽然很穷,却是大自然的宠儿。葛翠琳就在大自然里长大。她回忆说,那时候,“高粱杆剥开,做成马车、灯笼,河边抓把泥巴,捏成碾磨盆碗,柳条儿苇叶儿作笛子,葫芦瓢作船荷叶当伞……”(《绿叶的梦》)那些由大自然编织的生活是童话的故乡,是她童年的梦。
在她还不识字的时候,祖母就一边纺线一边给她讲民间传说,她心中最早的那些动人故事就是那架陪伴祖母一生的纺车给她纺出来的。老祖母纺了一生的线,直到死她都没有忘记用了八十年的纺车。那纺车就是葛翠琳读到的第一篇童话。双目失明的爷爷,不得不离开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私塾教育,但却在家里天天背诵古文,葛翠琳虽然听不懂,但却喜欢爷爷那种苍凉的有着十分强烈节奏的吟诵之声。葛翠琳说,爷爷的声音是她记忆里永存的苍凉纪念。
葛翠琳童年在乐亭县立小学读书。这所小学原来是一座古庙,侧殿是教室,院子里有躺倒的石碑、残缺的石龟石狮子、生锈的大钟和高大的松树、阴暗的大殿,空旷而荒凉的院子里杂草丛生。葛翠琳就从这里开始迈上读书生活的第一个台阶。这个学校有一个身材瘦小而清秀、性格温柔而善良的女老师,她教学生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及外国儿童文学名著《万卡》和《爱的教育》。《小抄写员》。葛翠琳说:当老师读到最感人的地方时,“就停下来沉默着。这时候几十颗幼小的心灵,就和老师一起思索着,眼睛里含着泪水,回味着作品里的情景。我们的心离开了阴暗的教室,离开了荒凉偏僻的小镇,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童心就从那里一天天走向成熟。
每日,鸡一打鸣,天还不大亮,深沉的天空里还有星星眨眼睛,这时葛翠琳就背着书包往学校里跑。她回忆说:“我快走,星儿也跟着我快走,我停住脚,星儿也站住不动。星星代替妈妈送我上学,我感到很快活。寂静的大街上,只有我的身影移动着。嚓,嚓……前边传来脚步声,小巷里又跑出几个人影来,小伙伴们呼唤着,追赶着,奔跑到学校。我们把星星关在门外,就坐在教室里摇晃着身子背诵课文……”这就是他们的晨读。她常常是小同学中到学校最早的一个。背诵课文,葛翠琳总是一字不差地背下来。
虽然葛翠琳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充满了恐怖和苦难,但她的学校却是大自然的美丽童话。除了上课,老师还带他们采集各种鲜花和绿叶标本,并讲述关于它们的知识和趣闻。星期天,他们跑遍密密的树林、荒凉的坟地、杂草丛生的河边、画一样的田野、一道道土岗子,爬大树,钻林丛,笑声惊飞觅食的小鸟,“篮子里装满各种绿叶,嬉笑,打闹,把元宝树叶串成项链儿,用金黄色的兔丝于草做成戒指和手镯,豆角花挂在耳朵上,野菊花插满了小辫儿……”大自然里的许多事物,一起编制成葛翠琳的童年梦。
有一次下大雪,她到学校时同学还没到,她的手脚都冻僵了,她以为老师还没有起床,谁知老师早进了教室,还为学生生好了火。老师让她把那双冰凉的小手伸进她的衣袖,这使葛翠琳感动得流下泪来。等同学都来到教室,老师便为大家读起法国都德的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文中所讲的由于德国统治而不能学习祖国文字的那个不爱学习的小孩子的悔恨心情,使他们都感动得流下热泪。他们都想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也在遭受日本鬼子的蹂躏吗?《最后一课》的悲剧故事不是正在中国大地演出吗?
晨读之后,同学们轮流讲演;他们一遍又一遍,讲演这样的内容:
“……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不!我们几万万同跑将团结成一个巨人……”
“……外国人讥笑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不!中华民族将为自己的英雄儿女自豪,我们的国旗必定在全世界受到尊敬……”
“……外国人说中国的地图是一片桑叶,世界列强是蚕,正在一口一口地吃掉它,不!我们要振兴中华,使祖国日益强大,列强再不敢侵略我们祖国神圣的领土……”
后来她最喜欢的女老师到外乡教书去了。临走时老师把冰心的《南归》送给她。葛翠琳说,她没有礼物可送老师的,“只有把真挚的眼泪,滴落在她的怀里。”
葛翠琳是班上最用功的一个,也是班上功课最好的一个。那所小学是她走向人生的第一步,给她的印象极深,她回忆说:“有一天下课铃响了,同学们涌出教室,玩跳房子、踢毽子、滚铁球、拍皮球,嬉笑打闹,一片喧哗。操场上僻静的角落里,围着一堆大同学,她们坐在跳高栏的旁边,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我好奇地跑过去,站在旁边听,立刻被那激动的声音吸引住了。书里讲一个东北孩子,到处流亡,如何怀念家乡,盼望抗战的胜利……听故事的同学热泪盈眶,念故事的同学哽咽着,时时中断了朗读。我低着头,止不住的泪水滴落在沙土上,仿佛校园里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听见那个流亡的东北孩子诉说着祖国的苦难。突然,有同学惊慌地跑来,叫着:'日本宪兵查学来了,快,把书藏起来。'大家慌乱地把书埋在跳高栏旁边的沙坑里,有人还在上面踩了一个脚印儿。同学们站在老师身旁,望着日本宪兵和翻译官走进教室里进行检查,校园里一片寂静……”后来葛翠琳用小手曾数次翻遍沙坑,那本书终没有找到,既不知书名,也不知作者,但她找回了本能的爱国之心、正义感和同情怜悯之心,那个东北孩子一直在她的脑海里,日本宪兵搜查时的那种恐怖也一直在她脑海里。
一幕幕小学生活,那位女老师和那些小同学,那些不能忘怀的往事,都像闪烁的星光,这种天长地久的人生馈赠,一直保留到现在。
二
小学毕业后,葛翠琳到北京求学,因考试成绩优秀而得以进入北京崇慈女子中学免费学习。为了学习英文,她学习英文本《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的学习毅力,献身科学的精神,强烈的爱国之心,第一次在她面前竖起一块人生路标: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立志苦读理科,献身人类科学事业。然而,在共和国的黎明之前,年轻人的激情把她推入了迎接太阳升起的热烈人群之中——在北京崇慈女子中学毕业前夕,她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参加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回到中学里积极参与组织读书会,办图书馆,阅读各种进步图书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组织理化实验小组,团结进步同学参加学运。
中国特殊的历史命运,终于把她同自然科学分开,高中毕业她考取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之后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她参加歌咏队,演戏,自编自演,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于是不知不觉,便和文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命运之舟终于也将她载入另一个港湾,使一个曾经立志要当科学家的少女由一个也曾经喜欢童话故事的孩子真正走进了童话之中——那里风和日丽,美丽的沙滩上戏要着无数天真的儿童少年。她爱那个港湾,因为她爱少年儿童,因为那里是人生的起点,从那里,孩子们可以高扬起真善美的风帆,将人生之舟驶向大海,怀着真善美的信念走向世界。
在那里,葛翠琳一呆就是一生。
她终于离开学校,走进了文艺界。1949年至1950年,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北京《新民报》、《北京儿童报》等处发表了《千百万老师》、《灯下语》、《家信》等诗歌和散文。之后,她又发表了一些童话和剧本。五十年代葛翠琳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的活动,老作家曾给她许多帮助和指导,使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许多故事一下子都浮出了记忆的海面。那时她常去农村,“在秋天的场院里,严冬夜晚的热炕上,在夏季的瓜棚菜园里,春天青草吐芽的放牧场上;在热闹的小客店里,长途运输的大主上,在老农民小憩的茶桌旁……我听到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这些故事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吸引我,感动我。”这时期,她搜集了大量